一、新问题
国内出现了一个新问题(也有人争论说这是一个早就已经提出并解决了的问题):文学已死,抑或没有死?这个问题如此紧迫,让希利斯・米勒的中文版译者决定将米勒的新书《论文学》“On Literature”的书名及时地改成了《文学死了吗》。美国解构主义大师能够替我们回
好在这本书类似于哈罗德・布鲁姆写的那本《西方正典》,是出版商替广大读者着想、向文学研究大家提出写作要求的书:简明扼要,直接面对问题。所以这不是那种令人退避三舍的书――那种书即使在回答“文学死了吗”这样直接的问题时,也首先会以令人敬畏的耐心辨析如下几个问题:一,什么是“文学”?二,什么是“死”?要解决第一个问题,先要问,什么是“什么”?甚至,什么是“是”……
为普通读者考虑,希利斯・米勒没有这样做,但这个工作在此刻看来似乎是不可或缺的。既然不断有人在热忱而殷勤地宣告“文学之死”,而在某些时刻,我们的确会产生文学“不在场”的感觉,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先问一下文学是什么?文学除了在抒情的意义上、在私人的意义上是个“梦”之外,它在更现实的层面上首先还是一个具有自身传统的建制。它由生产系统和评价系统构成,前者由教育、写作、发表、出版组成,后者由研究机构、专业杂志和大众媒体组成。“梦”可以死去,“建制”却很难死去。就是说,那些急迫的报信人谈的有可能是“梦”之死。因此,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报信人一问再问,甚至我们还要反躬自问:什么是文学之死?什么是死?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太多的人从自己放弃阅读那一天起,便宣布那一天就是他所面对的读物死去的日子。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的,在他的那个小宇宙里,局部的死亡――其实是溃疡――已经开始。虽然“文学之死”有数不清的意义,如果审视那些葬礼报信者的说法,我们会发现关于文学之死的众多意义围绕着阅读的终结,而阅读的终结的主要原因据说在于,报信者所认定的写作质量的普遍降低。
我不仅假定“文学之死”的宣告只是一种地区性症候,并且,我还要假定那只是他们报信人自己的病。正如一个思想者所说的那样,几乎每个以启示式语调谈论“**之死”的人,都远没有轻易地打发掉死者;那些讣告――那不过是他们与自己身上的幽灵搏斗时的呓语而已。
写到这里,我发现斯皮瓦克斩钉截铁的解构风格的论断,如果用在报信人身上是有其合理性的:“所有的结论都是临时拼凑出来的”。所谓“文学之死”,只是无力去思索混乱现状时发出的愤懑而含混的诅咒。
二、米勒的“文学之死”
米勒在本书中提到了“文学之死”这个问题,但无论他在原著中写下的“literature”还是在译本中出现的“文学”,其实和我们所说的“文学”是不一样的。他指出:“现代文学观,是被研究性大学以及为大学做预备的低等学校教育创造出来的。”也就是说,所谓的“文学观”并非是一个先验的“主体”,而是被建构出来的,或者说它只不过是一种话语的产物。文学的“死”,必然与“研究性大学”的研究方式有关,或者和“低等学校”与“研究性大学”建构方式的脱节有关――相比较而言,在中国则是文学的生产与评价机制的脱节。
关于文学之死,米勒的态度是暧昧的。当然他会经常提到文学之死,诸如正是研究性大学的“文化研究”的兴起在造成文学的死亡、文学理论的繁荣标志着文学的死亡、修辞阅读和文化研究无疑促成了文学的死亡等。
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米勒的说法,我们会发现他一直都没有认定这一死亡或这一事实的完成。关于文学之死,他只是在假定意义上去谈。第一章第一节的题目是《再见吧,文学?》这表明,他更愿意去质问这一说法,他的兴趣是去探寻造成文学死亡的原因。某个研究米勒的国内专家没有把握住米勒这句话:“很多人觉得文学的处境可能已岌岌可危……理论不仅记录了文学即将死亡(文学当然不会死亡),同时又促成了这一‘不死之死’”。该专家的理解是,米勒认为文学“死而不亡”。米勒在该书中有强调文学的这一幽灵特性吗?米勒曾动情地写道:“对深嵌在你的文化中的某物,只有当其隐退到历史深处时,你才能清楚地看到它”。也就是说他强调的其实是在这生死关头去重新定位文学。有一种认识论认为,当某物消失时,我们才能精确地衡量它的价值。对作家来讲,一个词的意义往往在它被删去的那一刻才明亮起来。失去一个珍爱之物甚或是爱人的那一刻,往事会照亮该物该人,并且往事会自动排序,固化为一个有意义的结构。
国内学术界讨论该问题方式往往是这样的:以前,文学非常吸引人;现在,出现了更有趣的娱乐方式(网络游戏、电视等),这些造成了对文学的冲击。在冲击面前,文学被边缘化了,或者干脆来个响词:“死了”。解救办法是什么?就是在人们的关注点中寻找最后的机会。他们提出的“机会”在我看来具有两面性,一面是极端世俗性的:既然人们都在关注金融,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写一篇金融小说?另一端: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最缺乏的其实是精神方面的救赎,那么文学就应该担当这一使命。后一种指导方式尤其令我扼腕:文学已自顾不暇,还想通过拯救别人来拯救自己?这两种说法陈陈相因,已经被说了很久。从它们被重复的时间跨度来看就可知它们是无效的。不过,它的功效在别处:我们可以在将来辨认出这些说法的重复者身上没有一滴学术血液。
米勒固然没有明确提出“文学之死”的看法,但我猜想他的看法其实是:文学的死亡永远在到来中。它的复活(或说苏醒过程)正如雪莱在《诗辨》中说的“创造的心灵仿佛一块暗淡下去的煤炭,某种不可见的力量,如同一阵阵风吹醒了它,让它发出短暂的光芒”。
三、文学如何可能
布赖恩・狄龙在《泰晤士报文学增刊》上撰文评价米勒该书时说:“该书的任务并非是面临现代科技大举入侵时夺回文学的老一套尝试,而是在雄心勃勃地努力去回应那些虚拟现实时确立我们的基石”。
文学在新媒体统治的新世界的可能性在哪里?它不可能又玩出什么新招数去迎战虚拟现实、电视或网络游戏――米勒甚至愿意承认这些游戏方式的正当性――它只是印刷时代的诞生物,“一本书就是放在口袋里的可便携的梦幻编织机”。
这种梦幻编织机随着时间的推移,所纺织的产品越来越精密,直到马拉美、乔伊斯、史蒂文思――请允许我谨慎地添上李贺的名字以便对照――作品的出现,这些作品吁请读者回到文学的表面,它们的神奇语言“强迫读者注意语言的表面,而不是透过它,到达一个虚拟的现实”。面对这些作品,人们才意识到文学把语言正常的指称性转移或悬搁起来。文学当然对它自身遭遇到的不同理解都来者不拒,但那些对于目的性进行戏弄的文学作品,其语言的表面的吸引力更大,这才是文学吸引人的地方。即使传统的定义中也有这一内容: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。
那些文化研究者,无数次企图打开所谓文学作品背后的秘密。发掘活动一旦开始,不发现秘密是不会罢休的。一般而言,发掘活动也总能发掘出它想找到的东西。文学具有的梦幻性质让人害怕,人们害怕它在灌输种族、性别、民族、阶级的危险信条或不公正的信条。弥尔顿《失乐园》中隐藏的歧视女性的倾向一旦表露无疑,它的魔力就丧失了。从我们的角度来看,文学就是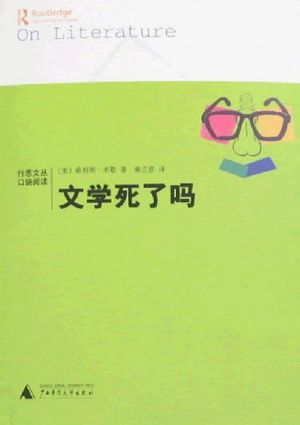 被归纳中心思想这一活动害死的。霍普金斯(Gerard
Manley
Hopkins)说过,文学作品是“反的、崭新的、少的、奇特的”。这是从文学呈现出来的效果而言。如果从女性主义、后殖民主义等角度看,文学的这种奇特效果必然绑定着某种固化的意义。这种固化的意义一直在给阅读者洗脑。他们的说法是这样的:文学当然是有益的,但必须去除――至少是指出或挑明文学中的那些洗脑因素,文学才能为人类提供更健康的服务。
被归纳中心思想这一活动害死的。霍普金斯(Gerard
Manley
Hopkins)说过,文学作品是“反的、崭新的、少的、奇特的”。这是从文学呈现出来的效果而言。如果从女性主义、后殖民主义等角度看,文学的这种奇特效果必然绑定着某种固化的意义。这种固化的意义一直在给阅读者洗脑。他们的说法是这样的:文学当然是有益的,但必须去除――至少是指出或挑明文学中的那些洗脑因素,文学才能为人类提供更健康的服务。
如何挽救文学?米勒当然不会扮演给未来文学算命或指路的角色。他认为挽救文学的任务落在阅读者身上。米勒鼓吹要“天真地、孩子般地投身到阅读中去,没有怀疑、保留或者质询。读者和所读故事间的关系,就如同恋爱。两种情况下,都是要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对方”。
阅读是某种“癫狂”,要搁置根深蒂固的“批评”或怀疑的阅读习惯。这种阅读方式当然令人生疑,因为表面上看来这不是一种“聪明的阅读”。但每个阅读者都必须选择:是进行“主动献出自己”的阅读,还是进行那种想着每本书都会洗脑的阅读?如果是后者,书就必须被质询、抵抗、去其神秘、去其魔力、重新将其纳入历史、尤其是虚假而错综的意识形态的历史。
(《文学死了吗》,【美】希利斯・米勒著,秦立彦译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,23.00元)
(本文编辑:朱岳)
